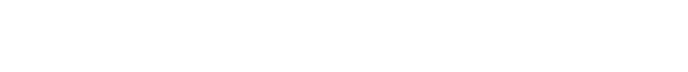■演讲人:邹广文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六教 ■演讲时间:二○一六年二月
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外在标志,通常所指的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而这里所讲的技术时代,则主要是指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开启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以资本与市场为表现方式的社会发展时代。在今天,科学与技术构成的这束“普照光”照耀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广泛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更是意味着技术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干预并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技术时代是人类的转折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为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对科学技术寄托了太多的期望,因而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所印证。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也同样普遍重视科学技术,而人文学术、文化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往往不知不觉被淡化和边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口号典型体现了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功利态度。而一旦文化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配角,我们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被颠倒了。
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自觉审视技术给我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竭的前进动力,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诸多矛盾、普遍存在各种严重问题时,重建人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代文明演进与理性精神
自资本主义文明登上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技术理性的发展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伊始,资本主义从萌芽中开始成长。资本主义文明来到世间,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但资本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天然特性,有其背离人们良好意愿的倾向,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同时也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即马克思是用辩证的历史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把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拖入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可见,技术的极大推动力是与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是使技术彰显其现实力量的助推器。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大放异彩的背后,其实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从近代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理性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文化最强音。无论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所言“人为自然界立法”,从这些哲学家的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出人类理性有多么的自信。从文化哲学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将西方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演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7世纪的“理性启蒙”。通常我们把17世纪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世纪。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觉醒,理性开始从宗教神学的蒙昧当中走出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主旨就是让人从宗教神学的光环中走出来。“把人所拥有的还给人”——这是近代文艺复兴的核心口号。而人从神的光环中走出来,人的世俗生活世界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在17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和向机器化生产的过渡,促使技术科学和数学急速发展;在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很多启蒙思想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霍布斯、伽利略等。笛卡尔哲学把人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思”是判定“在”之合理性的前提,强调“真理”问题只有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并去接受“我思”的检验和审判,才有资格去指导人的现实社会生活。
18世纪的“理性独立”。18世纪是理性独立的世纪,理性作为一种“光明的力量”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被普遍予以接受,并与宗教神学的“蒙昧的力量”划清了界限。理直气壮地去彰显人类主体精神的力量,勇敢、独立、自由地运用理性去面对世界,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就是18世纪主流文化诉求。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将“理性”这一表达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向全世界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18世纪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主编了《百科全书》,此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大百科全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系统阐释了理性对世界的全面性意义。狄德罗因此成为法国著名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在百科全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达朗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霍尔巴赫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18世纪的法国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
19世纪的“理性崇拜”。经过18世纪的全面理性启蒙,在19世纪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地、天等基本学科完成了分化,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运用日臻成熟,成了可以面对一切的解剖刀。恩格斯就曾经感慨地说19世纪是建立体系的世纪,认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仿佛谁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我们可以用三本书来代表19世纪的文化精神:1812年黑格尔的《逻辑学》发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三本书的象征意义在于用理性揭示了人的思维、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黑格尔的《逻辑学》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整部《逻辑学》讲的就是思维规律,他用理性建构了他的思维大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理性的“解剖刀”破解了人类自然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它的跨时代意义就在于把整个宇宙、自然的进化,包括人的进化都试图用一种理性的逻辑去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用理性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之在19世纪,理性成为可以解剖世界各个层面的“解剖刀”,“理性至上、人性至善”可以说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坚信不疑的价值理念。
20世纪的“理性反思”。20世纪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拐点,我们称之为理性反思的世纪。为什么要反思理性?因为20世纪的发展出了问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简直让我们刻骨铭心——在人类理性的一路凯歌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灾难?世界大战颠覆了人类的古典理想,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人类开始反思:理性是至上的吗?人性是至善的吗?1945年8月6日,20世纪的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得知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在极度震惊之余,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爱因斯坦还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通往人类战争毁灭的道路,是由我们这个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亲手铺就的。”晚年的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哲学家,他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反思着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有近90%的科学家直接、间接地从事着和军事有关的研究工作。人类最先进的理性和技术恰恰成为人类濒临毁灭的最危险因素。缘于此,20世纪的人文学者开始对“理性”进行自觉地反思,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等。哲学家尼采则在《快乐的科学》中宣称“上帝死了”——代表古典理性精神的那个理性死掉了。在文学领域,加缪的《局外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恶心》等作品,也从不同侧面表达出了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
技术时代的文化问题
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力,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生活之间的日益分裂。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明显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其中的“御”“射”就是一种技术要求。古时候人被要求“全面发展”,既要懂礼,又要懂乐,还要懂得射箭、赶车、书法、数学等知识。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是被归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这个大树上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以及人文。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去开发人的潜质,塑造人格。这就为古代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每个人能够学习到各种技能,以适应有机的社会生活。唯如此古希腊才涌现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整个学科也越分越细,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专家大都专精于某一特殊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全面发展的通才。这也许就是人类分工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体现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分工却又将人束缚在某个固定的职位上,无暇顾及其他,久而久之导致了人的片面性发展。而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开始了越来越分裂的态势,自然科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理性主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关怀让位于商业利润以及人的各种欲望追求。
当工业技术文明处在上升的时期,人类欢呼雀跃、憧憬着理性与技术能让人类渐入佳境、过上美好生活。但冷静思考我们会看到,人类理性在今天的滥觞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曾统计,20世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远高于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技术这把双刃剑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科学技术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精神、技术理性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而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人既需要人文,也需要技术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诺曾经在《两种文化》中描述了在大学里理工科学者与人文学者相互轻视的状况,指出双方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已达到相互不理解,甚至相互厌恶的境界。斯诺认为“人文”和“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分化和难以沟通,这是有效解决世界问题与矛盾的最大障碍。诚然,技术和人文对应于不同的需求层次。自然科学从总体来讲,就是满足人的肉体和生理需要的学问;而人文学科是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学科,其表达的是人的方向性、目的性关怀,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心理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就曾强调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瘸子”。其实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这也就表明科学一定要有方向,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为的划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所以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因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
对于科学和人文的融合问题,我们从人类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中或许能找到借鉴和启示。在古代,科技和人文还没有分开,但到了近代,二者的分化却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当技术无孔不入侵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重返古代的科学人文融合模式就越来越难了。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世俗化了,注重当下、崇尚实用,这不啻是整个社会的世俗景观。世俗化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社会就难免步入普遍平庸的时代,这就难以重新找回有机的社会发展模式,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融合就会愈加困难。
生活实践的人文关怀
加强人文关怀、重建人文精神已成了我们今天社会发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什么是人文精神?简单说来是一种为了人、关注人、理解人、把人当成人的思想情怀,倡导人文精神就是要求我们要在目的层面关心人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提出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把人当成人,而不要把人当成物,当成手段和工具。但在现今中国的市场经济生活实践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交往关系,常常将他人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与手段。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是非常需要着力加强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关切。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但是人文精神不变。有人把人文精神具体解读为人本、个人、自由,认为这是人文精神的三块基石,我比较赞同。“人本”就是以人为本、人是目的;“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价值,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关乎人类精神超越性的表征。
重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其根本点在于明确社会发展的目的性指向,赋予社会发展以恒常的价值与意义,以确保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可持续性。基于这一价值诉求来审视我们当今的生活实践,我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放弃思考。在全球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实践背景下,大众文化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消费形式。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中,大众文化产品被大批量、同一化的生产出来。但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产品往往是一种诉诸感性娱乐的、无深度的、平面化的消费形式,大众如果一味沉湎于对这类精神产品的狂热追求,必然淡化高雅的、严肃的、批判性文化的发展。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放弃思考,回避灵魂深处的真实渴求,人生的意义追寻也势必被冲淡了。
第二是躲避崇高。曾经,老百姓对充斥于社会的各种虚假崇高表现出了明显的拒斥。但问题在于,当虚假的崇高被消解之后,我们是否要严肃的追问:我们的社会还需不需要真实的崇高?可惜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大众的感性狂欢遮蔽了崇高的光辉,尤其在当代中国,信任、信仰的危机日益严重,“崇高”越来越遥不可及。老人在路上跌倒,无人敢扶。面对诸多社会不公人们不敢仗义执言,“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道义?在信任危机的环境下,这些道德观念经不住世俗、现实的考验,无人敢做好事,无人愿意崇高。这样,崇高的信念就渐渐被人们回避甚至淡忘了。
第三是拒绝时间。时下,快节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常态。似乎每个人都很忙,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知自己在忙什么,忙得没有方向感。改革开放,中国用了短短30年走完了西方150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发现“快”的背后出现很多问题:快常常不好——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虚假浮夸充斥社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快节奏的活,在快节奏中我们变得浮躁,心灵失去了宁静。古印第安人有句谚语说得很好:“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这一谚语发人深省: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但是忙的有精神关怀有目的追求吗?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流云小诗》中有一句话:“白云在天空飘荡,人群在都会中匆忙。”这句诗形象地折射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场景。的确,我们都在脚踏实地,但是我们有时间仰望星空吗?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每个人在无方向的、拒绝时间的忙,即使是人与人之间也常常是压缩时间的、功利化的交往,结果是人际关系变得日趋紧张和陌生。
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这三个问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导致的个人生活的碎片化、实用化。由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进一步衍生出了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把欲望刺激得太强烈了,我们过多的关注物质的占有和量的扩张,而忽略了内心的平衡,忽略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在追寻物质的过程中,反而失去了人性当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因此,要走出放弃思考、躲避崇高、拒绝时间的误区,就需要使技术与人文达到真正的统一,合理控制引导个人的欲望,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现代人精神家园的重建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类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需要在纷繁陈杂的经验世界寻找一个生活的理由,即为人生安身立命。重建技术与人文的统一,就是让我们的心灵重新找回心灵的充实和安宁。诚然,幸福作为一种身心和谐的感受,当然是和物质满足有一定关系。人不能画饼充饥,但是我们却不能把物质享受看成是生活的唯一目的。英国有一句民谚:“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们不能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而要实现心灵的充实与宁静,就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第一是重建我们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简单说来就是人们在公共空间里所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现代化拓展了人们的交往时空,这要求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必须遵循一些简单的、起码的行为准则。环顾当下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人们交往中公私空间不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私人空间也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好多人到了公共场所不知道遵守公共规则,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这是与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相悖的。所以,一个人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和教育,就是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到了公共场合,要遵守公共规则,讲求公德规范。
第二是要培养阳光心态。阳光心态是一种积极、达观、向上、进取的心智模式。今天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各种物质的诱惑,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扰动我们的心灵,现代社会快节奏所造成的压力使得我们的幸福感在下降。善于进行积极正面的心理暗示,增强人生的励志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阳光心态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特别是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如果心理太脆弱,就不能坦然地适应这个社会。培育阳光心态也就是养成一颗平常心,做到宠辱不惊——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当面对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要能够头脑清晰,守住自我,泰然处之。
第三是要学会赞美他人,学会感恩。赞美与感恩,目的在于营造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敢于赞美别人是心态健康的表现,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往往最不敢赞美别人。感恩既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现在是我们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但环顾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恩意识越来越缺乏。而培育感恩意识,是一个人步入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因此,要做到心里有别人,要学会换位思考。感恩教育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量变引起质变,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们要学会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换位思考。当你在社会上别人哪怕给你一丁点帮助,你都要对别人表达感谢,因为这是一个积累社会正能量的过程。
最后,就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是马克思当年所憧憬的理想,具体是指克服了人的异化状态、拥有健全自我意识、具有完整精神生活的人。现在的社会使人越来越专业化、碎片化,除了自己这个专业这点东西,其他不会了,不熟悉了。而一个完整的人应该善于展示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呼唤完整的人应该是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着丰富关系的人,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稳定的联系,并充分展开着自己的生命表现形态的人,自我通过构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进而成为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邹广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国成均馆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